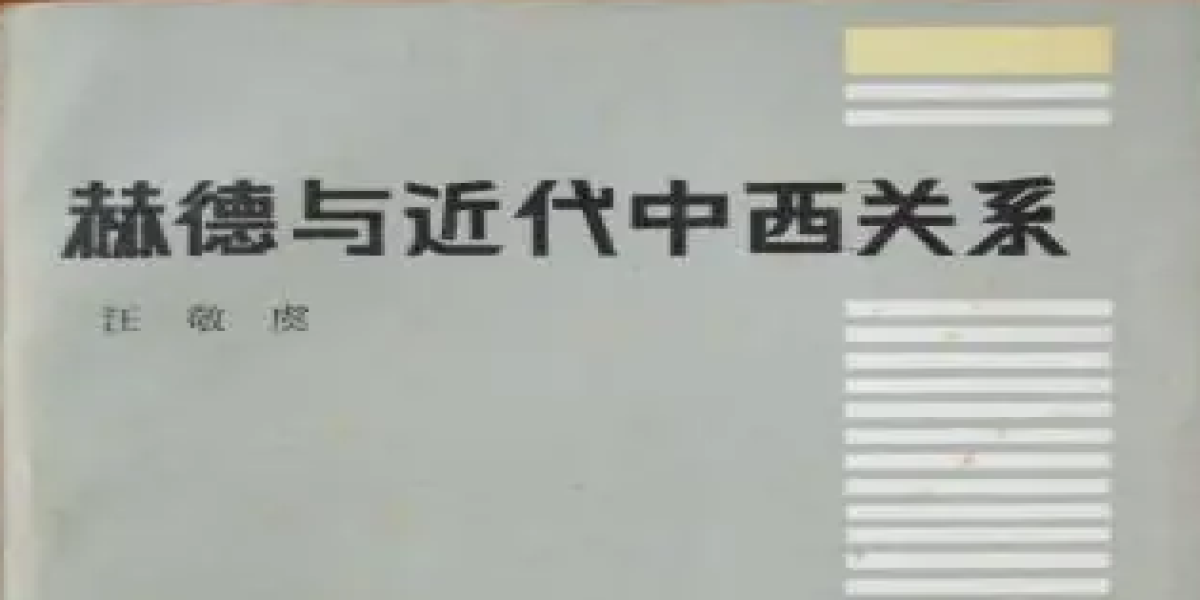在中国海关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英国人赫德(R.Hart)是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无论是赞扬抑或是反对他的人,都不能否认他曾起过的重要历史作用。这种强烈的反差固然与阶级、民族立场和价值观念有关,但却毕竟说明他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即是近年来国内赫德研究的力作之一。作为对汪先生极为尊敬的晚辈,笔者试图对此书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期望得到批评和指教。
第一,如何看待赫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汪著一开始就将赫德的历史活动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以及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进程联系起来,认为由赫德贯穿始终的中国近代史,仅仅是一部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一个古老封建帝国向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沉沦史(第5~6页),因而对于赫德的历史作用也作了全面的否定。这不仅是这本专著的主导思想,也是汪先生长期研究的一个思维特点。笔者认为,这样的概括和评价似乎是不够全面的。
在本文论及的历史时期中,中西关系的发展应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剥削中国人民与中国社会本身近代化不断深入扩展的统一过程。赫德所参与的西方资产阶级逼迫、诱使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活动,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将西方近代社会的某些思想和制度移植到中国,使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外国的事物”,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社会,扩大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从而打破了中国过去那种建立在封建制度基础之上的天朝礼仪及其片面设想的朝贡外交的模式,也产生了西方资产阶级不愿见到的后果。赫德晚年已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治中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时代发展趋势。如果说,中国过去在强权面前的屈从和沉沦是西方能够认可的唯一“理性”选择的话,那么,正在觉醒的中国人民决不能继续甘于屈从和沉沦,而是要尽快摆脱长期遭受的封建束缚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成为真正平等和独立的民族。“用睡眠来作譬喻,它(中国)已睡了很久,现在终于醒过来了,它的每一个成员正在激起中国人的感情:中国是中国人的,外国人滚出去!”
赫德承认,所有这一切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华活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笔者认为,从长期隔绝的中西文化相互联系交流的宏观角度来观察,不加强中外往来,不了解世界情势,就不可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形成推翻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更谈不上争取独立自由和谋求社会进步。况且,中国与西方联系的日益紧密,本身就标志着整个中国传统秩序的逐步瓦解,而赫德及其他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使近代中国日益深入地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潮流之中,增加了中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加速了中国传统封建秩序的瓦解过程。
依赖是一个很带争议的名词。西方经济学界有关依赖理论本身有许多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关于什么是决定依赖的基本因素的说法是各不相同的。在近代,频繁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既无能力也不可能在国际上形成独树一帜的力量,因而总是需要外在的平衡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清朝统政者支持赫德对中国政治、经济进行改革,其目的或许是希望最大限度减少中国的依赖程度。但历史事实是中国一步步向西方靠拢,受西方箝制,难以建立本身的独立形象。无论如何,这种依顺关系表明清政府在赫德等人的帮助下开始谋求在国际关系中找寻出路。相比过去那种以自欺欺人的闭关政策抗拒在世界上孤立的冷酷现实,不接受国际交往的惯例的做法,清政府对西方的依赖关系似乎不应当简单予以否定。因为这种现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科学分析,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打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笔者认为,资本扩张造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必然要求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依赖西方,放弃民族权利,做资本的附庸。同时,资本压迫本身也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运动,从而促进中国社会自身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决不仅仅是一部沉沦的历史;赫德的历史作用也决不应再用过去的尺度全面予以否定。
第二,如何评价赫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从赫德初涉中国政坛所提出的《局外旁观论》到其后几十次呈上的改造清政府的改革方案来看,他本人多少具有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善意,说赫德没有任何使中国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或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动机,不仅在逻辑上难以成立,也不尊重近代历史的事实。赫德自我表白说:“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中国自强”。他曾多次对清帝国的弊病进行过较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他所提出的一些革旧图新的建议,许多都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如他曾提出“凡有外国可效之善法,应学应办”,并将之看作是“跻中国于强盛和开拓进步之路的手段”。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赫德的这些思想是有远见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理解了社会时势发展的规律和要求。
就拿赫德对中国海关的改造来说,汪敬虞先生承认,在赫德进入海关之前,中国封建海关“没有行使征税和管理海关行政的有效能力”(第36页)而“在海关税务司管理之下,外国商人的走私逃税不那么容易了”(第55页)。甚至他也客观地指出,赫德对海关的改造,“或者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新事物的引进,或者是增进对资本主义世界新事物的认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有积极意义的一面”(第81~82页)。但从全书来看,汪先生对此所持的全面否定态度是十分显然的。他反复强调,“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一套都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第11页)。
众所周知,国家主权是政治学的概念。实际上,赫德进入海关之前,中国海关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性质,正象陈诗启教授所指出的:“虽属独立,却独立不了;虽属自主,却自主不了”。可见中国海关所表现出的国家主权已经名存实亡,以此来评判赫德对中国海关的改造显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况且,研究历史并不能仅仅从政治学角度出发,而应该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样才能客观揭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循序发展的一般过程,才能准确地评价赫德改造中国海关的功过得失。
笔者不拟在这里详细评述赫德与中国海关近代化的关系,但只需指出一点,即随着近代中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改造旧海关的关税制度及作业方式已是势在必行。赫德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面貌和需要对中国海关进行逐步改造,将西方海关先进的行政管理制度引进中国,这一点是完全应该肯定的。另外,他还运用国际法的某些原则,帮助清政府对各国商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过一些交涉,甚至与外国领事、公使也据理力争,并聘用外国律师参与法律诉讼,迫使西方国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中国作出让步,限制了外国奸商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缓和了当时的中外矛盾,客观上对发展正常的中外贸易和保障中国的税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汪先生却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史实(即使不是主要方面),而仅仅以抽象的国家固有权利全面否定赫德的客观努力,把赫德领导下的整个海关工作的作用笼统看成是消极的,这难免令人感到遗憾。
汪先生在书中还提到了赫德给中国引进的其它一些近代设施,如海关邮政制度、海务体系以及京师同文馆等等,但统统给予极为低调的处理。汪先生认为,这些“都是首先服务于他们(指西方侵略者-引者)的利益,他们的目地,都不是什么向中国引进新的技术,至少首先不是这样,而是为自己攫取利润,至少首先是这样”(第369页)。甚至他将京师同文馆与会审公廨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从根本上说“是统一在一个实体之中,它们有共同的目的和方向”,都是“为了适应外国侵略的需要”(第364页)。笔者认为,即使邮政、海务、同文馆的确是为了满足外国侵略者的需要,但近代中国社会此时不也同样有这个需要吗?而且对中国来说这种需要甚至更为迫切。
这种以主观动机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唯一依据的作法,无疑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一般说来一定的主观动机能够产生出相应的客观效果,但二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动机所产生的效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想,结果从他的行动中产生出某种别的东西,这种东西诚然包含在他的行动之中,但却在他的意图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功过是非,究竟是依据他的主观动机呢,还是他的客观效果呢?笔者认为,应将他的言与行、动机与效果全面权衡,应当着重分析他的客观效果。
例如赫德亲手办理的海关邮政及海务工作,其中确实有加速外国资产阶级在华侵略的目的和作用,可在另一方面,也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把中国的通讯业务和海务工作迅速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中国航运、邮传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客观的公益性质是无法抹煞的。
再如京师同文馆,虽然赫德主观意识上并不一定是“为中国培养新式教育和人才”,但只要认真了解近代中国教育史的人,谁也无法否认同文馆在开创中国近代教育、培养中国各类人才方面所起到的客观历史作用。刘铭传在《台设西学堂招选生徒延聘西师立案折》中曾这样说道:“自京师设立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师,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升,人才蔚起,海防洋务、利赖良多”。这些作用与赫德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认为他是一个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给予全盘否定。我们不否定在一定的条件下恶在伦理上的确定性,也不认为善恶的辩证法是相对主义的,但在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作用时必须防止过分注重主观动机伦理化的倾向,把历史的进步当作倒退。
虽然赫德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引进了一些新的社会因素,但灾难深重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近代化。特殊的历史条件使赫德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先行者,注定了他在中国实行改革的失败命运。赫德曾委屈地说他“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这种结果也不难想见。可以说,赫德的悲剧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使这种要求无法实现的客观条件之间冲突的悲剧。笔者认为,象汪著那样全面否定赫德的一切客观努力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汪敬虞先生的这部著作,长达300多页,与赫德毫无关系的背景叙述就占三分之一强,有100多页。这对全面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背景,固然有一定必要性(虽然对本书的范围来说所逾稍微多了一些),但汪先生将所有这些侵略活动都算在赫德头上,认为“他都有份,他插手了一切”(第12页)这未免有点过分了,不仅不合情理,实际上也站不住脚。
汪先生在书中宣称他不是“国粹主义者”,他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优于中国封建主义的国粹。但他强调:“问题在于正确地区别西方文明本身和西方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西方文明是一回事,西方入侵者手中的文明,又是一回事。”(第363页)。笔者同意文化和文明存在着社会界限、民族界限以及特定的阶级界限,但笔者反对人为地对西方文化及其西方资产阶级入侵者进行一刀两断的切割,或给予主观的取舍。在中国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东进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外压成为促进内部变革因素增长的契,而伴随西方人侵者传播而至的西方文明不仅仅是西方入侵者所挟以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手段,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借鉴和中国人民摄取外来文化、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外部因素。正象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所指出的:“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手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文明的传播方式是否是强制性的,传播者是何人,对中国社会的促进都是巨大的。区分“西方文明”和“西方入侵者手中的西方文明”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笔者认为,《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反映了汪先生的那种先入为主的心理效应。他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抽象的理性作为衡量以往历史的尺度,往往因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入侵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在汪先生看来,既然西方人侵者是全面反动的,那么由他们传入的西方文明也都成为不合理的东西,都应该贴上侵略的标签进行痛斥,并加以彻底否定,乃至全部扔进垃圾堆。这样就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同时也否定了西方文明。这样做虽然满足了抽象的逻辑要求,也不失其进步的性质,但却脱离了历史的具体情形,也妨碍了对西方文明的价值作出科学的结论,不仅很难缩短我们与历史人物真实之间的差距,而且最终将导致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
笔者认为,对赫德之评价,应不断克服过去那种敌我、正反、善恶的人物两极化的思维定式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教条偏见,深入开掘出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既要看到他在时间阶段上的变化,也应分析出他的各个方面,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他对中国近代化作出一定贡献而讳言他的罪过,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罪过而否定他的一切积极作用,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譬如赫德帮助清政府举借的各种洋债,有的是政治性的借款,有的则是一般的高利贷性质的借款,并非都有政治野心和政治作用,不应笼统地认为接受外来资本一定有害,而应该有所区别。
再如,汪著中多处就赫德参与的各种中外谈判,给予了激烈的批评。须知任何人参与谈判都必然存在着两种心理要素,既要合乎谈判人员的动机,也要合乎谈判对手的需要,只有这二者的统一,才能形成有效的谈判谋略,推动谈判活动的发展。谈判是满足需求的过程,必定要建立在双方有某些需求而又期望得以实现的基础之上,其出发点应是努力寻求最佳途径。在不断争取自己一方利益的同时,也要尽量使对方感到满意,而不导致对其利益的损害。在近代中外力量悬殊的历史条件下,更不能不考虑这一点,要予以具体分析,不能一看到赫德在一些谈判中提出中国让步的意见就大加指责,应该区分开赫德所提出的让步哪些意味着中国自身利益和目标的牺牲,哪些则是一的“欲取姑予”的策略。这些也是汪著中所欠缺的。
今天人们的观念体系正在从过去近乎单一、封闭、僵化的旧模式中挣脱出来,向着一个开放性的新观念体系推进。对赫德的研究也是这样。人们不应再用旧的尺度去臧否历史人物,也很难同意一成不变地去全面否定或者肯定谁人的历史作用。当然,新旧更替是个扬弃过程。一方面新观念对旧观念的否定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确定界限,另一方面,又是对旧观念的合理成份和有价值因素的继承和吸收。这样就可以为新旧观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体现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我们之所以重视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其意义亦在于此。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